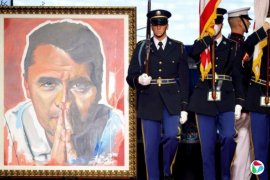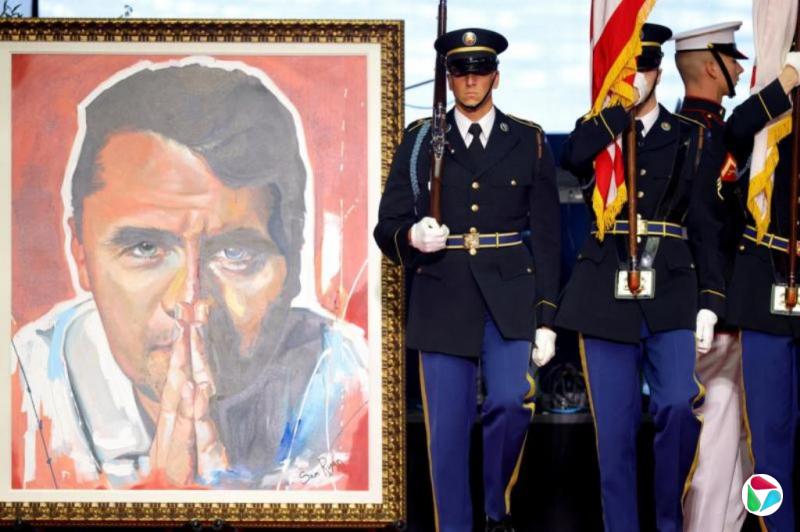
查理·柯克9月10日在公开演讲中遇刺身亡,是美国政坛继2024年7月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遇刺未遂之后,影响最大的一次带有政治企图的暗杀。在此之前的美国政坛重大政治暗杀事件,笔者认为要追述到肯尼迪总统(1963年)以及马丁·路德·金(1968年),二人遇刺都是由于触动当时美国社会中固化了的种族问题和利益集团,用生命换来美国社会的永久性变革。相反,柯克的身亡非但没有产生变革的火花,反而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更加困惑。
这不禁让笔者思考,一位社区大学的辍学生,如何在14年间,成长为能够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并且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问题都侃侃而谈的政治活动家?柯克是某些报纸吹捧的“政治活动家”,还是浅薄的政治网红?是什么导致对他的政治暗杀?
在柯克的演说视频中,笔者注意到他的说话特点:语速快、声调高、傲慢,即使在自己思路受阻时,依然保持咄咄逼人的气势。视频中的争论对手,往往是年轻大学生,在这样的气势压迫下,鲜有能和他匹敌的。笔者隐约感到,柯克似乎并不在乎讨论议题的内容,更有兴趣的是在辩论(或者争论中)战胜对方,即便须要使用某些辩论技巧也在所不惜,比如偷换概念。
在一次校园辩论中,一位学生提出“(以色列为什么被允许)剥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自治权”问题,柯克反问“为什么他们(巴勒斯坦人)不干脆搬去约旦成为约旦的一部分”,接着他又开启一个新话题:“请告诉我什么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身份”。如此,他把这次辩论主题从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自治权,转向历史,并在后续的辩论中,始终围绕历史上是否有“巴勒斯坦人”这个民族概念,最终,他傲慢地教育对面的学生:历史上从来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片土地叫朱迪亚—撒玛利亚(Judea Samaria)。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搜索一下“朱迪亚—撒玛利亚”这个概念的历史来源和在当下的意义,但是柯克这里引用这个模糊不清的历史和政治概念,显然是有意识地避开关于生存权和自治权的辩论,让原来的辩论无法继续,迷惑对手,以达到取胜的目的。类似的辩论技巧,在柯克的演说视频中出现不止一次。
但是,柯克的校园辩论也不乏亮点。比如在讨论非法移民相关的政治经济议题中,他提出“我们不是一个只看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这个说法迎来围观学生一片喝彩。确实,功利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侵蚀,一直就是现当代文化批判所关注的议题之一,比如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20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当代英国文学批评家)。“功利主义算计的视角……尽可能以非个性的方式呈现自身。就仿佛这个世界只包含不需要度过各自人生的不同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人(或’自我’)的许多化身”(《人、品格与道德》,威廉斯,1981年);利润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优先事项”(伊格尔顿)。
只关注经济增长如GDP而忽视个体的复杂性、忽视人文关怀,注定会让现代社会的未来蒙上阴影。如果我们将柯克所说的上帝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将成为能够抗衡功利主义的批判性人文主义关怀。当然,这也可能走向纯粹的宗教裁判所,成为原教旨主义。不管怎样,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辩论中,最重要的并非胜负,而是提出这些针锋相对的论点,引发人们思考。柯克则过于看重辩论的胜负,往往在辩论过程中强行输出自己观点,不惜使用一些隐蔽的辩论技巧或者干脆强词夺理。正是这些幼稚的思维和套路,使得他的演说失去批判的光环,演变成傲慢的诡辩。
今天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社会,人们往往把自己或他人定义为左派或右派,前者代表某种进步主义,后者则是代表某种保守主义。柯克经常公开把自己定义为敬畏上帝的保守主义者,并且将他对总统特朗普各种政策的无保留支持,都归入保守主义,在很多场合表达对特朗普及治下美国的崇拜和热爱。甚至在关于非法移民的辩论演讲中,对一位二代移民在校生说“你应该庆幸现在生活在美国100多年来最伟大的时代”。
左派和右派目的都是获取更大的权与利
在关于信仰的演说中,柯克引用《新约》中耶稣关于“盐和光”的利他性、包容性感动学生,但是在另外一场关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辩论中,又毫不讳言“我们(美国)以支持以色列作为交换,获取以色列的某些先进武器和科技产品”,继而引用《圣经》中关于基督徒应该保护犹太人的段落,为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道义上的支持。这些逻辑混乱的说辞,被柯克用非凡的演说才能揉合在一起。
笔者认为,今天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左派大部分根本算不上左派,而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利己主义者;右派也不能算是右派,而是原教旨主义者。所谓左派通过推行激进的文化改革,树立自己的进步形象,比如2024年6月5日发布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规定:拒绝变性学生使用按性别区分的区域,如卫生间,将构成违法。右派则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内坦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这些所谓的左派和右派,目的都是在美国的议会、政府获取自己更大的权与利,只不过手段不同。与媒体共谋,把自己的行为贴上左派、自由派,亦或右派、保守派的标签,只是为了构建归属感,并且从所有认为自己脑门上贴着某个标签的选民身上,获取流量和支持,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成为现实,从中渔利。对于这些人而言,公众整体利益是第二位的,削弱和消灭对手才是第一位。比如,最近特朗普就宣称,对于敢批评他的媒体,是不是应该吊销他们的从业牌照。
在柯克刺杀事件后,特朗普和他的幕僚迅速将刺杀事件归咎于“极端左派”,并宣称已经开始讨论甄别和打击那些组织。这从侧面说明贴标签的威力,标签所能引发的共鸣和厌恶一样多。
虽然真实世界并不是非左即右,黑白分明,但刺客和受害者都被贴上标签,非友即敌,最终演变成以命相博。
柯克生前经常在演讲中表达自己提倡公开辩论的初衷:真理不辩不明。但是他在辩论中所展现出的幼稚、傲慢和强势,又似乎有违自己的初衷。笔者倾听过马丁·路德·金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演讲,知道什么才是有号召力的、逻辑严谨的演说。学识、才华、诚实、谦卑,缺一不可,这都是柯克所欠缺的。即便他能凭借技巧,在激烈的辩论中让对手一时语塞,之后人们稍加回味,就感到疑点重重,甚至觉得被欺骗而愤怒。这也是不少美国大学中的年轻人对柯克产生厌恶的原因,认为他言辞煽动有余,公允不足,充满恶意,经不起推敲。
自从2016年特朗普首次使用推特(现改称X)作为总统竞选宣传渠道,社媒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突变。在140个字的短消息里,经常蕴含着煽动、欺骗、猎奇和仇恨。2021年1月竞选连任失败的特朗普煽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造成人员伤亡,并因此遭到美国众议院弹劾(这是他第一任期内遭到的第二次弹劾)。2025年6月,明尼苏达州两位州议员被刺杀,一死一伤。
美国政治生态与民主政治渐行渐远,走向戾气十足的暴力强权路线。白宫内外的政见不合,经常激化为凶险的明争暗斗,普通民众私下已经忌惮谈论某些敏感政治话题。伴随着美国政治生态的异化,柯克也从宣扬保守主义的网红意见领袖,转变为特朗普执政体系中的重要宣传官媒。正是新技术造就的畸形政治生态,加上柯克自身的不足,造就今天美国最年轻的政治牺牲品。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服务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