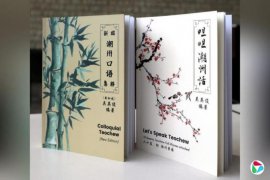拜读黄顺杰先生《地铁故障频频 信任如何维系》(9月21日想法版)一文,深有同感。黄文指出地铁事故过多,非仅影响民众出行,还会动摇社会信心。因为本地交通模式是建立在普罗大众放弃私人拥车,由政府提供可靠、便利的公共交通的无形契约之上。
现代都市,公交先行已成共识。尤其是地窄人稠的新加坡,如此方能达成共赢。因此,本地压缩私车使用空间,通过拥车证与电子收费等,将拥车成本抬升至全球最高水平。在此背景下,地铁与巴士不再是选项,而是必需品。全球许多城市大量投入物力人力,以提升公交系统的吸引力。但只要几次严重的不良体验,乘客便会考虑转回不具持续性的出行方式,结果导致共输的局面。
首先说一句公道话,新加坡的轨道交通存有先天性挑战。比如本地气温高、多雨潮湿,会造成设备老化加速;南北线与东西线本身已是数十年前的旧系统,老化导致的稳定性下降势所必然;再加上高密度使用与每天维护窗口时间有限,以及缺乏线路设计上的冗余与分流,线路扩张较快等原因,也使某一条线上的故障,容易造成系统性出行困难。
即便如此,我们还可从更深层次来探讨新加坡的轨道交通模式。我们可以与台北的地铁稍作比较。新加坡的模式为: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包括轨道、车辆等重资产,但运营权则交给运营商。这种模式其实在巴士车系统中运转良好,像SMRT等运营商总体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巴士车运营对系统性要求低,哪怕车辆或车长出了问题,也能迅速更换;有线路堵塞,也能及时换线,不会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地铁则不同,它从无孤立事件,一旦出事就是系统问题。因为在地铁系统中,无论是信号、供电、轨道、列车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事,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也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出行。
问题是,两家轨道交通运营商,一家为淡马锡控股(SMRT),一家为上市公司(SBS Transit),是否要兼顾财务可持续性的目标?换言之,在新加坡,虽然轨道交通是全民绝对的刚需,却仍须在市场化逻辑下运行。作为承包运营商,盈利目标是否会与“维护绝对可靠性”相冲突?因为作为企业,背后始终有一根市场盈利的指挥棒。当然,作为政府方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对运营商具有统筹规划的权责,也会利用市场化激励机制来鼓励运营商保持正点率,甚至对于故障还会有惩罚机制。但显然,这些奖惩机制并未起到期待的效果。
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地铁高层会推诿说这不是系统性问题,因为作为盈利性企业,乘客只是必须购买服务的对象。压低成本,获得利润才是永远的企业内部刚性需求。运营商可能因成本压力,而推迟设备更新或压缩维护,进而影响可靠性。如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则至少不会如此高高在上,能体会每日通勤挤车者的切肤之痛吧。因为新加坡普罗大众无论多么心存怨念,最终都只能选择公共交通系统。他们的怨气最终也不会只是发泄到运营商,而是可能会朝向政府。因为当公共交通已成为强制性消费品时,盈利效率导向最终可能会转化为对乘客的不公平负担。
与此相对,台北的捷运系统则由市政府全资建设、运营并维护。因此,它可能就不会徘徊在盈利与维持高效服务的不同目标之间,首尾失据。所以在“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等衡量运营质量的指标上,远高于新加坡同行。这可能更体现它在制度与地铁上的“系统性优势”,不仅票价稳定、延误少,乘客满意度也高。
新加坡向来强调公共决策的财务可持续性与效率,因此选择一条折中之道,这当然极具内在的合理性。但在乘客缺乏替代选择(因拥车证政策等因素)时,地铁应被视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工具。当乘客在扭曲的市场化逻辑下承担服务风险时,我们可能应在战略取向上,更多地向地铁系统的稳定性方面倾斜;否则,它真可能侵蚀新加坡的整体社会信任。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