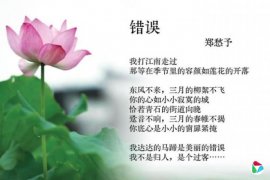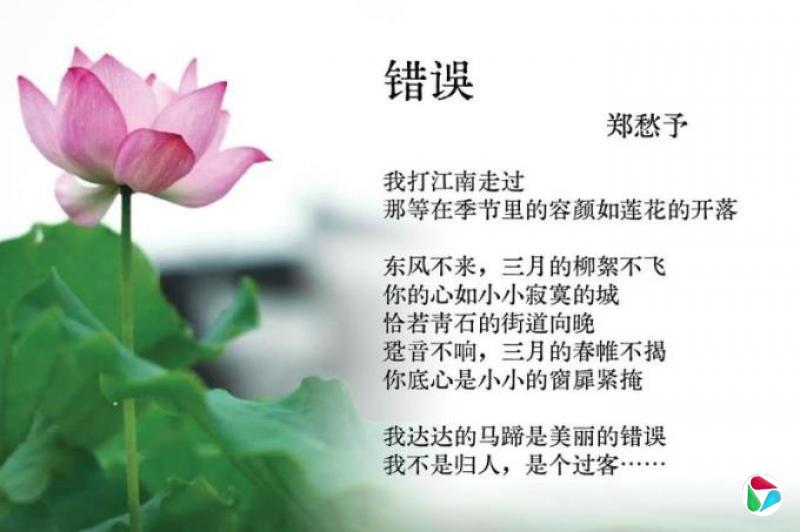
人的一生,无论学习或成长,也无论顺流逆流,悲欢离合中,都不会没有歌。有很多的故事、记忆,是带着音符的,此为岁月如歌的诠释之一。但那个歌中有诗、有情怀的年代,应该回不去了。
上个月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刚打完球,同事发来郑愁予过世的即时新闻,一时百感交集。
我先是心里,试着把《错误》背诵个遍,发现挑战过关,字句都没忘却。更重要的,是江南、东风、柳絮……那些个意象如昔,触动也依旧。
我不是记忆力特好,过目不忘,而是当年和友伴们把《错误》不知唱过了多少遍。很多音乐大师,都给了这首诗音符,像李泰祥、像张世儫,但最爱的始终是罗大佑版本。
郑愁予自称是“现代诗的古典派”,罗大佑的《错误》,不妨也可看成是华文流行乐“古典风”的滥觞。当然尝试者还很多,如侯德健的《归去来兮》、陈幸蕙和陈志远合作的《浮生千山路》。他们都可说是周杰伦、方文山的最早引路人,也才有后来的《烟花易冷》(减掉嘻哈的混搭),以及《东风破》《青花瓷》《菊花台》等等。
作者已死 解读权是众人的
罗大佑的《错误》,比郑愁予的多出这两句:
哎呀妹子妳那如泣如诉的琴声,可曾道出妳那幽怨哀伤的梦?
哎呀妹子妳那温柔纤纤的玉手,可曾挽住那似铁郎君的心?
也许原诗的“短—长—短”三个小节,在音乐上须要衔接(李泰祥用的是“啦啦啦……”),也可能第二和第三小节太跳跃了,诗可以,歌不行。罗大佑的添加,正面一些的评价是风格大致贴近,负面的认为有违和感,甚至破坏了。无论如何,年轻罗大佑对自己的才华,应该是自负到不行。
有人说《错误》写的是乡愁,也有人理解为情诗,我就属于这一少数派,认为诗人是在感伤自己只是个过客,走不进所爱之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把他的另一首诗《情妇》(在一青石的小城,住着我的情妇……)放在一起对照、遐想。不是吗?一个被情妇深爱着、苦等着,还可以情绪勒索到底;而另一个面对的,是永远的“春帷不揭”“窗扉紧掩”……
但毫无疑问,闺怨是最大公约数,连郑愁予自己也这般解释过;至于罗大佑补上的两句,更是赤裸裸了。只是我还是要抬杠:妹子的芳心,也可以另有所属啊,而“我”选择了没有结果的爱情,何尝不也是“美丽的错误”?况且,不是有“作者已死”的理论流派,即认为创作一旦完成,进入到所有人的自由解读和“再创作”空间,就已非作者所属了,任何的感悟和诠释,都没有绝对对错。
OK,闺怨就闺怨吧,这可是中国诗词亘古的主题之一,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有好几首,像《中谷有蓷》中的 “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还给了我们一个今天还在用的成语。
后来的闺怨名篇,几百上千首不止。最早被广为传唱的,也许是王昌龄的“闺中少妇不知愁……”这首七绝题目就是《闺怨》。然后还有白居易《长相思 · 汴水流》、冯延巳(一说欧阳修)《蝶恋花 · 庭院深深深几许》、李之仪《卜算子 · 我住长江头》等等等,一首比一首厉害。
从男人到女人 古今闺怨诗大比拼
古代女性受教育的比率很低,闺怨总由男性“代笔”。不否认一些真有共情能力,懂女人心的,但据已故叶嘉莹先生的说法,更多是借女人发挥,“怨”自己的怀才不遇、仕途多舛罢了。要到了李清照,才以《声声慢》力压一众男人,夺得第一名。她开头那七组14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就别出心裁,堪称绝唱。今时流行音乐,叠字佳作我首选台湾作词人厉曼婷的《离人》,里头前后用了11组叠字,既是修辞手段,相信也是对前人的致敬。
李清照是宋代闺怨文学大神,但少有人知道,几乎同期还有一位神秘女子,也写过一首几乎能和她叫板的《鹊桥仙 · 说盟说誓》词。女子只留下“蜀妓”的署名,姓氏无从查考,可见当时性工作者地位之卑微。也由于两人的不同出身阶层,作品风格大相径庭,一个婉约典雅、欲语还休;另一个直白、大胆,限于篇幅,全词就不引述了,但有两句表达对薄情郎无时无刻的思念,大家可能读过:“……相思已是不曾闲,又(更)哪得功夫咒你。”是的,或许还唱过,就是潘越云的《相思已是不曾闲》。
这首歌很好听,也仿了古调,曲风很“中国”。内容则是当代闺怨,写一个女人对太平洋另一头恋人的朝思暮想。作词人台湾旅美学者许芥昱下笔相当含蓄,但巧妙借用蜀妓的这两句,把爱与怨的张力拉满。可惜,1982年,《相思已是不曾闲》的曲还未完成,许芥昱就因一场大雨山崩意外,死在美国的居所里。歌词里的“怎奈春雨把巉崖都化作软泥”,似乎冥冥中早有预言,知情者听了,无不唏嘘。
在古代,诗与乐不分家,所以管文艺的机构,甚至所采集的诗或民歌,都称为“乐府”。但现代诗不容易入乐,还好到了上世纪70年代,台湾校园内有人开始为诗写歌,校园外则早有琼瑶在引领风骚,不断把古人的笔法,化用到自己填的歌词中,渐渐地,“诗”歌终于又出现了。
罗大佑在还没当上愤青,批判现实时,就写了好一些现代诗歌曲。《乡愁四韵》(余光中诗)是《错误》之外,另一首文学味道醇厚的作品。歌中的吉他声,乍听还以为是古琴奏出来的。比罗大佑更早把《乡愁四韵》谱成曲的,还有被公认为校园民歌之父的杨炫。罗、杨这两个版本,当年台湾人唱的是故土乡愁;而我们,更多是文化乡愁吧。
还有徐志摩忧伤的《歌》(译自一首英诗)。很多人以为《歌》是为电影《闪亮的日子》创作的,但罗大佑早在读大二时就写出来了。其实徐志摩的诗,当时几乎都入了乐,像《偶然》(陈秋霞曲)、《再别康桥》(李达涛曲),还有被大改了的《海韵》(左宏元曲),这首歌多数新加坡人只知道跟着邓丽君唱,不知道背后有徐志摩。
电影《闪亮的日子》里还有一首《兰花草》,因刘文正的关系,也是满大街都在唱。同样的,鲜少有人知道歌词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胡适的诗作《希望》。
歌中有诗 也就心中有诗
举这些个例子,无非是想说,那真是一段美好岁月。台湾诗坛、乐坛人才辈出,高手成就高手;加上有广大阅听群体的欣赏和买单,供需两端一同发力,最终大概在1990年前后来到巅峰。任何成长于这二三十年间的学子、年轻人,包括新加坡,只要遇上了,接触了,都会如痴如醉。也因为歌中有诗——古典,五四、现代的,心中也就多少有诗。那些批评流行音乐是靡靡之音、次文化的,我总觉得视野太窄,以致不得要领。
《早报》当年还办了几届的国际华文文艺营,郑愁予、余光中、痖弦、洛夫等都参与了,虽然没有时下男团、女团被追的疯狂场面,但毕竟是诗坛泰斗,对文青的吸引力还是巨大的。对了,有一年三毛也来了。她的词作很多,《橄榄树》就是她写的,虽然她曾说,有两句不是(难道是李泰祥?)。本地一位和三毛有交往的文人前辈还跟我说过:三毛说她只写了“橄榄树”三个字?!
报馆有一位70多岁的午夜德士师傅,说受英文教育,但莫名地喜欢台湾校园民歌,坐他的车总有听歌的福利。有一晚播出《梦田》,因已有N年没听到了,一下子恍如隔世,听老师傅哼着旋律,还有些小感动。老师傅或许知道歌唱者齐豫和潘越云,但作词人三毛,她的红尘来去,以及那些撒哈拉的故事,肯定都远在天边,闻所未闻吧。
和我们较贴近的,应该是《说时依旧》。诗是文艺营里,三毛朗诵后,交给初相识的年轻梁文福去写成歌的。歌的最感人处,是结尾最白最不像诗的两句:……家中孩儿等着你,等爸爸回家把饭开。据说这位爸爸,也就是三毛早年“真的真的真的爱过”的“你”,在她朗诵时,也在台下的某个角落。
以个人偏好来说,梁文福的“诗”歌,甚至是本地新谣,没有比周策纵的《我读过了他的酒窝》更“美不可言,爱不可说”了。我们报馆墙上,有这位已故国际著名汉学家及诗人送的“天人合一”书法。我每天走过,看着那歪歪的四个字,总突发奇想,如果写的是“酒窝”两个字也挺好的,有少年的暗恋、想象的美感,肯定更吸睛。
诗和音乐曾是台湾最强大的软实力输出,几乎没有哪个华人社会不受到影响。它先是在南大播下诗乐的种子,如《传灯》(张泛曲,杜南发诗),跟着在高中校园,润雨般大面积催生新谣春笋的生长。几乎同时,诗乐在彼岸转化为“诗曲”,生命力更为顽强,产生的佳作更多,像《流放是一种伤》(温任平诗,陈徽崇曲),时至今日,仍然是听一次感动一次。
一个回不去 也无法复刻的时代
人的一生,无论学习或成长,也无论顺流逆流,悲欢离合中,都不会没有歌。有很多的故事、记忆,是带着音符的,此为岁月如歌的诠释之一。
但那个歌中有诗、有情怀的年代,应该回不去了。政权更迭、课纲改变,台湾人的认同、审美以至精神面貌都已不复当年。中国大陆庞大的影音产业则太商业化了,总体给人失真、市侩的感觉。?抖音上洗脑神曲当道,要不就是对中国风的集体膜拜。当然中国风本身没问题,只是去到太尽,一些还走上奇技淫巧路子(像《左手指月》,根本就是让人炫技耍酷,而不是写来唱的)。早年,还有朴树《那些花儿》《平凡之路》这类让大学生风靡的诚意之作,但如今知音寥寥,已成了小众。
我们呢?你知道的,硬伤是语文能力普遍跟不上,和诗,已渐行渐远。
同事那天也在短信中感慨:郑愁予那一代人,也许只剩席慕蓉了。
席慕蓉的《出塞曲》,当年也曾和友伴们激情地唱过,但《一棵开花的树》才是她最美、最隽永的诗篇。遗憾的是,尝试写成歌的人很多,可就是一直等不到上上之作。从这个角度看,郑愁予是幸运的。“达达的马蹄”不只静态停留在书面,供背诵和赏析,还有好的音乐伴随,可以让人吟唱。
江南走过,一生漂泊。曾经的游子、过客,如今又远行去了。戴着他的桂冠。
那是闺怨的赛道,来到现代诗的这一百年间,他凭借《错误》赢得的。
虽然,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是一首情诗。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