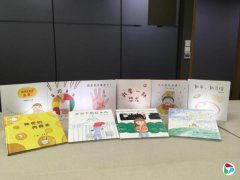在日常的阅读推广活动中,常常有人说,新加坡本地的华文绘本和儿童读物很少,要推广华文阅读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读物。还有人说,新加坡书写环境比较自由宽松,却难以看到题材更广的作品。然而,9月27日举行的“2025学前教育论坛”却可以刷新人们的认知,原来我们拥有的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我们拥有的比想象的多。
这次论坛由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和新加坡社科大学纳丹人力发展学院主办,主讲嘉宾都是新加坡本地的儿童绘本作家和儿童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主题是“六十年文化沉淀与创意交流携手学前教育成长之路”。童书绘本与学前教育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这次论坛也可谓梳理了一次新加坡建国以来华文童书绘本的创作脉络。
新加坡的儿童文学和绘本作家是否真的寥寥无几呢?主讲嘉宾之一的儿童文学作家陈帅说,在演讲前采访了近20位本地作家,包括余广达、李文良、小邝、林文佩、椰子(刘聚洪)、曾慧婷、黄淑君,以及虽然作品在外地出版但居住在本地的绘本作家戴芸和晓苏(郭少青)等。原来本地有许多人在为儿童写故事,也不缺乏会写又会画的人才,例如阿果、虎威、林文佩、李文良等。曾慧婷的《菲菲,你真棒!》这本书的插画师是郭宏驯,他不仅会画,自己也写绘本故事,如《臭臭》和《奇妙的纱笼》。本地插画师余广达的作品就更多,国内外已出版200本左右,最近他和林得楠合作的《辛苦了,红头巾》还二度入围大众书局的读者票选好书奖。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郑婉妮博士同时也是绘本作家,她和作家虎威、贾立明也分别在论坛上分享自己的绘本创作历程。社科大学教授陈如意最后还分享了本地华文分级阅读的丰富读本。听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梳理,才发现原来新加坡还有那么多优秀的绘本和儿童故事书,我们拥有的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阅读就像一条隐秘的金桥,让孩童可以通往外部世界。如何架设这条金桥,是父母和教师的功课,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但是,新加坡的儿童文学创作起步是比较晚的。陈如意介绍说,1920至40年代,新马地区才开始出现华文儿童文学。金丁创作的《谁说我们年纪小》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标志着我们开始尝试为孩子发声。经过二战期间的停滞和建国初期的低潮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本地涌现不少华文少儿读物,《少年月刊》《新加坡儿童》《欢乐儿童》等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稳定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才开始形成。到1990年代,在出版社、作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儿童文学才算有了坚实基础。她说:“建国60年历程,本土儿童文学创作可谓从无到有,从借鉴到原创,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学前教育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今天再去书店和图书馆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领域代表作家周粲、雨青(欧阳想想)、林昉、林琼、洪生、陈森汉(向风)、陈彦、何若锦、筝心等人的作品,已经很少见到或者很少被借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社会须要共同关注的。
精神产品更需要政府真金白银支持
文艺创作和别的社会产品不同,精神产品更需要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其实,近年来一些本地作家的作品在初版售罄之后,也很难再版。旧作难再版,出版社或囿于日渐高涨的印刷成本,也须叩问人们是否仍有阅读热情。足够的阅读热情和真实的买单,才能支撑起创作生态,现实却是作者一直在坚持“靠爱发电”。
也许有人会问,阅读真的那么重要吗?忝为这次论坛主讲嘉宾之一的我觉得,阅读至少可以让孩子“心里有世界,眼中有他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未来的世界是冷漠的,那么就要学会理解差异。很多时候,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起源于相互不能理解。
目前,我正在创作一个关于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故事集,几乎所有出版社都认为这是一个小众话题,难以打开市场。可是,在新加坡,80%的特需生都在普通学校就读。如果说融合教育是充满金光的理想,那么可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参与论坛的一些学前教育教师都殷切表达他们很需要这样的绘本,因为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故事。在故事中,小朋友能充分享受在现实与非现实世界中的穿梭,并从中感受到隐含的生活要义。
当我们在生活中知道如何看待自闭症谱系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读写障碍儿童,以及有其他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时,知道该如何与他们相处时,我们就不仅在促进相互的理解,也在升级成更好版本的自我,社会也相应地升级为更文明的版本。
儿童的生活经验是有限的,最初,他们都是在绘本和故事书里寻找突破。小邝在接受陈帅访问时说:“我心中期待的阅读是可以在故事里看见自己和发现各种不同的生活,也能感受到文字和图画带来的各种启发、喜悦与想象。”出版超过50本书的林文佩说:“绘本最大的能耐是它能留下某种情感或画面,在记忆中停留很久。阅读的意义不一定是教育,有时候只是内心深处那一点触动。”郑婉妮说,绘本的语言是诗意与日常交织的。它以极简的文本说出深刻的情感。也正因此,更容易成为儿童最早的文化经验载体。
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还要致力于通过气味、空间、感官经验与生态互动,展现出文化如何在孩子的身体记忆与情感交流中被生成。
早期阅读是重要的,绘本和童书不仅对于群体的文化生成有意义,从儿童更广阔的成长来说,也意义非凡。其实,细想一下,我们拥有的,真的远比想象的多,缺乏的只是了解和推广。同时,我们拥有的又比想象的少,很多作品都受限于市场而难以出版,每出一本书都意味着巨大的投入,而本地作者长期以来都在“用爱发电”。虽然在儿童文学创作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作者们依然在奋力耕耘,但真正从创作到出版,还需要社会各界许多实际的支持。
作者是童书创作者、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