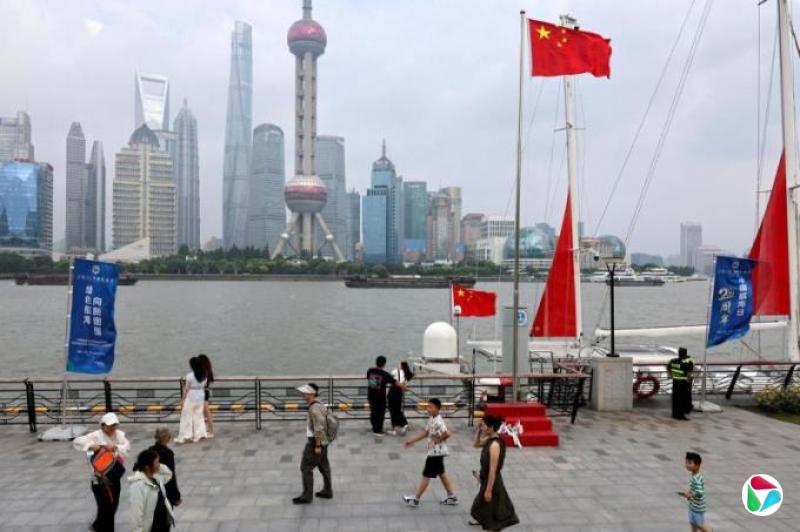
总结回顾,相比于第一次浪潮,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在全局影响、启蒙努力、市场发展、科技融合和人民受益等若干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起色和进步。但也必须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最核心关键,即思想、价值和体制的层面,第二次浪潮同样再次受阻。
所谓八零后到零零后等中国新生代,对1978年底召开的大陆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恐怕不甚了了。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是引领中国追求全面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或者说在经历浑沌—觉醒—革新—战败—变法—幻灭—共和—歧途的第一次中国现代化浪潮后,中国人痛定思痛,筚路蓝缕,为提升自己民族的文明高度和质量,追赶现代世界先进文明的步伐,绝处逢生再出发。
实事求是地讲,1978年中国毅然开启改革开放,并非关键一招,而是面对时代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别无选择,被迫突围求转机。
促成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对内纠正极左政治和瞎折腾,顺从与解放人民的意愿和智慧,释放与发挥人民的巨大潜力和创造力;对外亲近友好战后世界文明秩序,向美国、日本和西方开放,大量学习和引进先进文明、现代生产力、科技发展和市场运作模式,才促成数十年的快速进步腾飞。
必须清楚指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并非前无古人,实际上是自1840年中国步入近现代世界后,几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甚至流血牺牲所为之奋斗的现代化事业的一大组成部分和后续接力。历史和时间作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波三折,充满坎坷挫折。这180多年的艰难跋涉,主要可划分成1860年开始的第一次浪潮,及1978年底开始的第二次浪潮,前后正好相差两个甲子的时间。至于第三次浪潮将会何时启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目前尚属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景状态。
笔者以为, 对前两轮中国现代化浪潮的重要关键节点,如能做出一些比较深刻透彻的反思总结,对将要到来的第三次浪潮,必定会具备充分的警醒、启示和创新作用。相反,如果严重缺乏反省和忏悔能力,不断重复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和步入的歧途,就会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于停滞、倒退甚至前功尽弃的空前危险之中。
首先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匮乏现代化的先驱和原创,即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古代文明,没有能够主动催生向现代文明转型。在1840年之前,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等全方位,中国都是古代化,而非现代化。在1792年曾出现过一个重要节点,即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首次派官方贸易代表,出使清朝乾隆帝治下的中国,本希望借此出访打开东方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之门,并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
但中英双方的首轮交往,结果失望可悲,中国的古代脑子与英国的现代脑子完全无法沟通交流。中国一直是个老大农业文明国家,对工业、贸易及航海等概念淡漠,而英国当时已行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快车道上,发展堪称一日千里。英国人来访大谈贸易关系、外交关系、对大清朝官员来说,就如盲人摸象,天方夜谭。这其中的文明发展代差,在约50年后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显露无疑:英军以区区9000余人远征军,不远万里登陆中国并打败几十万清朝军队,清朝被迫赔款割地,令人触目惊心。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1860年前后,中国与东面的邻邦日本几乎同步开始民族的首轮改革开放大业,中国当时叫洋务运动,而日本叫明治维新。从名称也可看出两国图强的路径相当不同,日本更注重维新,而且是领导人率先垂范。日本采取的是全盘西化战略,领导人带头穿西装打领带,吃牛排喝牛奶,在政治体制设计和军队培训建设等方面,也是全面照抄西方作业。
“中体西用”的错误
这里想强调一点,所谓“全盘西化”在中文语境中,更多是个有感性色彩的贬义词,但过度咬文嚼字,却也经常掩盖一个简单和基本的道理:即向先进文明学习是个全面系统工程,如采取局部割裂和片面投机的做法,往往导致最后难得要领,错失真传。中国就是这样,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只注重学习先进的现代化手段、技术和装备,但思想、价值和体制建构,还是固守中国的古代化传统和积习。
表面上看,中国的意图是捍卫自身文化主体性,反对完全照抄他人作业,以防丧失自我。此种做法在一般常态局面下可以理解,但在遇到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转型这样的艰巨挑战时,日本式的壮士断腕、脱胎换骨举措,最后证明是收到更大更广的成效。在辩证哲学原理中,这叫做否定之否定,从而最后达到新的肯定。中国在甲午战败后试图亡羊补牢,推动“戊戌变法”,但最终还是无法跨越守旧顽固自闭的藩篱。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在第一轮改革开放实行40年后,中国北方竟然出现盲目仇外排外、强烈反智反文明、大肆破坏捣毁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所谓“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幕后起先有清朝官方的主使操纵,主要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欲对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赶尽杀绝,但遭到西方列强坚决反对阻止。慈禧恼羞成怒,试图借义和团之手打击报复洋人。民间的因素也深刻说明,40年的洋务运动可能影响到国家官僚、社会精英及知识界的层面,但却让普通百姓层面受益不大,民智未开,反而多遭盘剥,倍感失落,甲午战败更是激发民间激烈的民族情绪。
于是,民间的仇外排外情绪和行为集结起来,就形成义和团运动。但义和团的致命荒谬之处,在于试图以古代化对抗现代化,来挽救腐败落后的朝廷和国家。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结局注定是枉然和失败。更何况清朝一旦在权力统治遭威胁的时候,就出卖和背叛义和团以求自保,并反手对之进行针对和绞杀。“义和团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古代文明在现代文明的竞争面前大失体面和自尊,底层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无奈逆反和负面挣扎。
下一个关键节点是“中体西用”的错误改革方略,加上清朝爱新觉罗家族死抱最高权力和既得利益不放,最后导致第一波现代文明浪潮的低落退败。和平温和渐进的改革路线图,即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立宪,推动政治体制现代化,在清朝顽固派的残酷针对下,完全无法实现,也导致最终发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采用武力激进手段推翻帝制,走向共和。
但激进的革命模式,从纵向传统来讲,延续历代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窠臼;从横向借鉴而言,也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青年一代,不久开始属意马列主义的激进革命主张,并接受采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暴力夺权模式,埋下深重的伏笔。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思想,认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把世界瓜分完毕,于是俄罗斯这样的落后和非西方国家(注:其实从中国角度,沙皇俄国也是西方列强的一分子,而且瓜分霸占中国最起劲最凶狠),如果想自强崛起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打破旧有世界秩序,另起炉灶,才有成功的前途和希望。列宁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备相当的感召力和煽动性。
但列宁忽视或者没有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即西方列强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的自由民主法治也在不断自我进化和超越。二战前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为主导的旧世界秩序,也在战后为主权独立、民族自决、联合国协商协调机制、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所替代。战后现代文明秩序远非完美,但足以让列宁和斯大林所创造的苏联模式望尘莫及,愈发落伍掉队,最后在1991年底被彻底淘汰出局。
不仅如此,传统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也逐步走进死胡同。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处于山重水复的危机,也激发出第二轮现代化浪潮的滚滚而来,为中国和新一代中国人迎来柳暗花明的新局面。这两个甲子之后发生的第二轮现代化浪潮,成败与否,乃取决于中国能否充分反思和接受第一次浪潮的经验教训,战胜类似的激流险滩、问题挑战,走出更聪明、智慧和勇敢的新路。
总结回顾,相比于第一次浪潮,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在全局影响、启蒙努力、市场发展、科技融合和人民受益等若干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起色和进步。但也必须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最核心关键,即思想、价值和体制的层面,第一次浪潮所没有跨越的雷池,第二次浪潮也同样再次受阻,也因此导致第二次浪潮目前的大幅消退,后续乏力,几近夭折。
昨日虽已远去,前路依然茫茫。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势在必行,任重道远。中国的事情往往伴随物极必反的发展变化规律,当第二次浪潮进入彷徨和低迷状态时,也许预示和孕育着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继往开来,异军突起,即将奔涌在东方的广阔地平线上。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