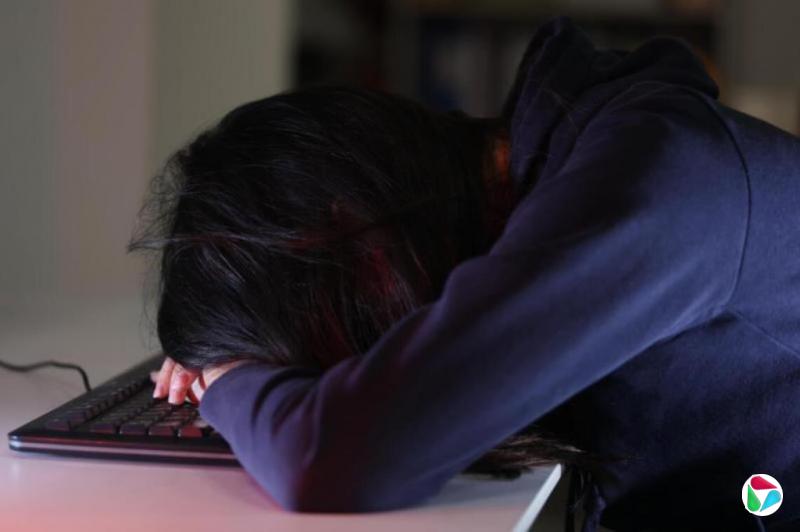
近几个月新马两国校园霸凌事件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我正好在Netflix看了令人窒息的《默杀》:初中生惠君长期遭受同学霸凌,最终从高处坠亡,由于主谋是校长女儿,学校上上下下的目击者都集体沉默。后来霸凌目标转向惠君闺蜜小彤,在她全身被涂胶、呈十字形悬吊于墙后,她母亲还是因为和校长的利益关系,选择隐忍。
现实中很多校园霸凌事件,都是这种旁观者集体视而不见的悲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校园暴力划分为四大类:身体暴力(肢体攻击等行为)、心理暴力(言语侮辱、社交排斥、谣言散播等)、性暴力(性骚扰、性胁迫等),以及网络欺凌(传播虚假信息、令人难堪的内容等)。
根据新加坡官方数据,2019年至2023年五年期间,中学和小学欺凌事件年均报案率,分别为每千名学生六起(0.6%)和两起(0.2%)。马来西亚教育部的数据则显示疫情后的2022年、2023年和2024年里,校园霸凌案分别为3883、6528和7681宗,以2022学年中小学生总人数约500万计算,当前校园霸凌率百分比应该是约0.15%,和新加坡数据相差不远。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在2024年对1010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约30%受访者声称曾遭受霸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针对4469名公立学生的研究也揭示,79.1%学生涉及霸凌行为,其中纯受害者占16.3%,兼具施害与受害双重身份者高达48.4%(引2021年7月《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健康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论文)。
这些数据显示,在新马两地,绝大多数校园霸凌事件都“密而不报”,导致官方记录在案的数据普遍被低估。环顾全世界,校园霸凌也是普遍存在的教育界难题。2023年UNESCO的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每三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人遭受霸凌影响。UNESCO在2019年整合《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GSHS)等国际数据发布的144国报告,也显示马来西亚11岁至15岁学生中,曾遭遇校园欺凌、参与肢体冲突及遭受肢体攻击的比率分别为21%、30%和29%,与印度尼西亚(21%、25%、34%)及泰国(33%、29%、30%)情况相近(新加坡数据暂缺)。研究同时揭示,霸凌次数越多,受害者学业成绩下降越严重。
在马来西亚,今年多起校园霸凌导致伤亡的案件屡见报端,其中沙巴州13岁女生扎拉命案未获妥善处理,不仅激起全民愤慨,更暴露出国家立法缺位、教育系统监管失效,以及社会长期沉默纵容的问题。这起悲剧虽推动政府考虑制定《反霸凌法》,但立法仅是第一步,马来西亚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在于执法不严的制度性缺陷、问责机制模糊、校方玩忽职守甚至包庇隐瞒,这些往往成为霸凌的帮凶,单靠法律条文恐难扭转积弊。
本区域亟需开展更多本土化研究
目前有关霸凌的研究报告,大多基于西方理论体系。这些报告可用作借鉴,却难以充分反映新马等国的多元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观念上的差异。因此,本区域亟需开展更多大型针对多元族群的本土化研究,从不同文化视角构建霸凌成因的解释框架。
最重要的是,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扫门前雪心态,让旁观学生(有时甚至包括原应保护受害者的教师、舍监等)选择沉默,无人站出来制止霸凌者,成了帮凶。
因此,根治校园霸凌需要制度修正和文化变革双轨并行,后者尤需教育工作者通过教育实现。在强化校方问责的同时,也要为教师提供实质支援,尤其是增聘专业心理辅导员,以构建完善的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10余年的普及,已使“电子保姆”深刻塑造青少年身心成长、性格和心态,不但导致年轻一代社交能力退化,也持续暴露于暴力、色情等有害内容。
约自10多年前起,笔者和同侪就已发现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在大学生群体激增;我们当时怀疑,长期高频率使用手机或社媒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并削弱对道德和社会议题的反思能力。一项涉及全球10万名18岁至24岁Z世代青年的最新研究,证实这一课堂观察:13岁前拥有智能手机和青年期较差的心智健康,存在显著关联,其中网络霸凌是重要中介因素。
笔者认同该论文作者提出的建议:为保障未来社会的身心健康发展,各国政府应效仿烟酒管制政策,立法禁止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
此外,笔者也认为本区域教育体系亟需推动以下两项变革:其一,教育并鼓励学生勇敢举报霸凌事件,彻底破除自扫门前雪的畏缩文化。其二,推行每日一善行动,要求师生每天在校园至少做一件好事。
当善意成为校园文化和根基,恶念自难滋生,霸凌也就无从立足。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分子遗传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