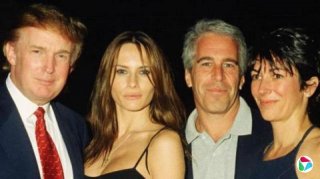只有通过制度化安排,才能让“常驻董事无权参与公司运营”的现实假设,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事实。
财政部与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7月14日共同启动《公司法及会计法(修订)条例草案》的公众咨询。根据官方资料,本次修订旨在实现四大目标:防止公司被滥用于非法目的、减轻公司的监管负担、保障股东权益,以及强化对公共会计师的监管制度。在减轻监管负担方面,草案提出包括允许唯一董事兼任公司秘书、取消部分财报和招股说明书替代声明的义务、豁免有股本的公众有限公司召开法定会议与编写法定报告的要求,以及取消注册办事处对公众开放三个小时的规定等。这些举措清楚体现政府力求简化公司合规流程,提升注册效率的意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常驻董事这一在实务中极为普遍的安排,却在此次修订中未获任何正面回应。根据《公司法》第145条,公司必须至少有一名新加坡本地常驻董事,因此大量外资公司依赖企业服务提供商提供“挂名董事”,以满足在地董事要求。虽然ACRA自2017年以来要求公司保存挂名董事登记册,并自2025年6月起将此类信息提交至中心登记册,供公众了解董事是否为“挂名”身份,但法律与监管并未清楚界定挂名董事在日常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范围。
更严重的是,尽管业界普遍将挂名董事视为仅履行形式职责,不参与实际运营或决策,但法院判例(如郑佳案)却并不承认“挂名董事”存在任何特殊免责待遇,而是按法定董事身份,直接对他施加予普通董事同等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司法态度令挂名董事无从通过“协议条款”主张免责地位。尽管挂名董事与实控人签订协议,明确指出“挂名董事无权参与公司运营”,但法院通常不承认这些协议,仍将他认定为履行董事职责,并据此施加责任。这一执法常态使得挂名董事及其服务商处于极高风险之下,缺乏制度保护。
与此同时,尽管企业服务提供商新政自2024年实施以来,已规定只有注册企业服务提供商,才能为公司安排挂名董事,并要求企业服务提供商开展尽职调查及资质核查等合规流程,但这些规定更多关注挂名董事的承办主体合规,而非在公司治理中具体职责的规定。结果是,挂名董事是否参与决策、签署合同、履行董事的法律义务等方面仍然模糊不清,缺乏统一制度支撑。
若修订草案最终出台而未对本地常驻董事角色做定义,会造成更广泛的问题。首先,常驻董事一旦因公司违法行为受到追责,身份即从“无权参与”跳跃至承担全部法定义务,风险急剧增加,而企业服务提供商无从有效转嫁风险。其二,外国股东与投资者对这一制度认知与纠结,会增加对新加坡营商风险的担忧,或迫使他们寻求更加复杂、冗长的合规路径。其三,法院与监管之间的制度脱节,可能导致司法判例裁决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损害ACRA简政放权的初衷。
因此,作为企业服务提供商从业者,笔者强烈呼吁ACRA能在本次修法中,新增“本地常驻董事标准化守则”,为这一角色制定统一指引,实现以下目的:
首先,应该明确区分“本地常驻董事”(Local Resident Director)和“挂名董事”(Nominee Diretor),把“本地常驻董事”的定义规范到“无权参与公司运营、决策和管理,并仅承担作为本地董事的制度性义务,如文件查看、年报申报、法定通讯接收等”,并要求只有本地企业服务商的从业人员,才能担任此职位,职责和法律义务与真正须要特殊规划的“挂名董事”不同。只有明确提供免责条款,常驻董事才能在法律上厘定职务与责任范围,避免误判。
其次,应制定标准协议模板。ACRA可发布含责任范围声明、免责条款、退出机制与风险告知等条款的常驻董事服务协议示范,而非让市场自行拼凑。此举将为企业服务提供商提供统一法律文本支持,降低商业纠纷和诉讼风险。
第三,守则必须结合企业服务提供商注册制度,构建背景调查机制。企业服务提供商应被要求,在每次常驻董事任命时完成资质调查,并按年度提交常驻董事职责声明,明确他“仅为本地董事,无实质控制权”。
第四,制度设计须与司法实践保持一致。建议ACRA将守则纳入可供法院参考的政策文件,从源头减少常驻董事职责争议,使守则推广成为衡量常驻董事行为合法性的核心标准。
只有通过上述制度化安排,才能真正让“常驻董事无权参与公司运营”的现实假设,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事实。这不仅能减少企业服务提供商和常驻董事的潜在风险,亦能显著降低常驻董事的成本,使得本地企业服务提供商在亚太地区更具市场竞争力。
作者是项目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