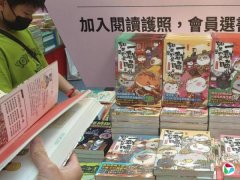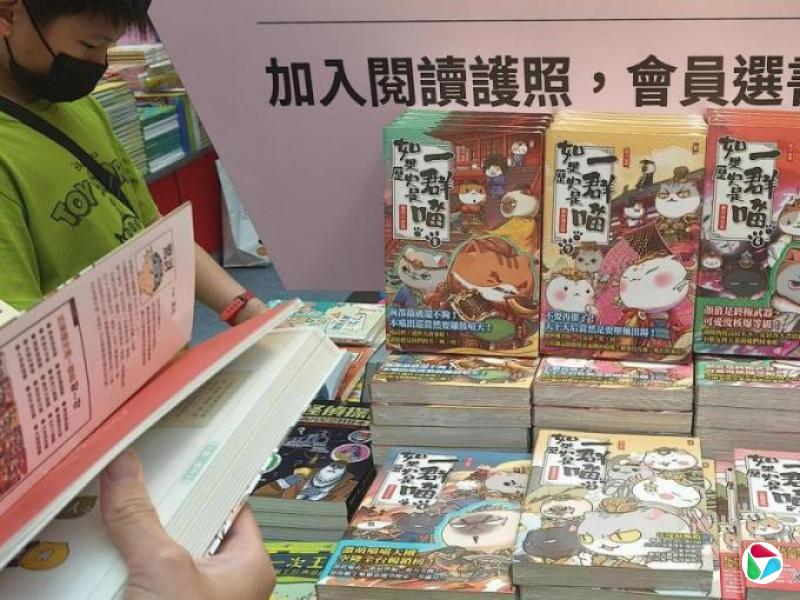
我常常听到以下的描述,甚至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表述。
孩子不喜欢华文!
孩子不喜欢华文阅读!
孩子不喜欢华文写作!
孩子觉得华文很难!
我突然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以上的说法,是不是能找到更数据化的论据?比如某某机构针对多少个什么年龄的孩子进行的调查,孩子通过审慎思考,认真回答问题之后,是不是依然会得出上述的结论?
我们抛开这几个暂时没有论证的问题不谈,就笔者去一些学校分享阅读和写作所见,很多孩子对于华文没有自信倒是普遍存在的。
关于自信这件事,作为教师或者家长,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表面上看,华文的自信来自识字量、阅读量、写字能力,作文能力以及成绩等等,有没有可能同时可以有另外的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有一次,我去一所学校分享写作。我跟同学说,要不,今天我们来写诗吧。不出所料,我看到同学面有难色,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两个小时时光的不期待,还有认命的状态。一个男生直截了当地说:“老师,我不会。”
他说得真好,因为我也不觉得我会,我要做的不是教怎么写诗,我要做的是一种寻找和尝试。所以我说,“你随便写”。他叹气,然后就真的随便写了。
他写的句子如下:我抬头,天上有一只小鸟,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全班哄堂大笑。
这情况糟糕吗?好像有点糟糕。可是,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心情来思考?全班大笑,是不是说明他们对诗歌有隐约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他们熟悉的诗歌?男生随便写,是不是表明他有写的能力,而不是他自己说的“不会写”,他只是不确定诗歌可以怎么写?男生写下的句子看起来不太像一首诗歌,可那是他脑海里看到的画面,他算不算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好的诗歌的开头呢?(它甚至让我想到鲁迅的“枣树”)。
我试着把他的句子变成下面的样子展示给学生看:
我抬头
天上有一只小鸟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样有没有更像诗歌一些?格式上好像有哦。
那如果再改一改,像这样:
我抬头
天上有一只小鸟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它会不会飞进一个孩子的梦里
会不会更有诗歌的味道呢?当时的我表扬孩子的尝试很棒,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会告诉他,他有写的能力,他做了尝试后,出现诗歌的雏形,他比他说的“不会写”要会得多一些。
我在好几所学校都用了梁文福的一首诗歌做例子,那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雨衣上
犹可闻到
那一场和你携手走过的向晚春雨
我问同学的问题是:你们喜欢哪个(些)字或词?为什么?
直到今天,除了“的”字,每个字(词)都有同学喜欢。也许你读到这篇文章,也可以问问自己,喜欢什么。
同学的表述极大丰富了我的思考边界。比如他们说喜欢“春雨”,因为好像感觉到雨的凉意,打在身上飘在脸上的感觉;比如他们说,“闻到”比“听到”“摸到”好,因为没想到是用鼻子,不是用耳朵和手;比如他们喜欢“向晚”,就是因为觉得还可以用另一个方式表示天快黑了;比如他们喜欢“携手”,觉得有温暖感;甚至有一个同学就是喜欢“雨衣”,因为他从小就喜欢雨衣。
我也表达我的喜欢是“犹可”两个字,事情过了那么久,可是那时的心情还在。这种情绪的延续,延续了那么久,久得我似乎能够看到那场雨,还有那场牵手。
你看,每个人都有感受。
如果我问的问题是:你们觉得哪个词语用得好?是不是会带有一种评判?评判会让孩子有一种比较感,有一种高低之分。可我问的问题是喜欢,每个人都有权利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诉说的是感受,而感受没有高低对错之分。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阿凡达2》。电影里,那个爸爸很清晰地对他的儿子说过两次:“Son, I see you”(儿子,我看到你),在电影院里的我热泪盈眶。我们每个人,不只是孩子,也包括大人和老人,我们都希望被看到、被听到。如果我们张开耳朵去听,有没有可能听到孩子不喜欢华文背后的不勇敢?有没有可能看到他努力表达了,却依然不尽如人意后的努力?有没有可能和孩子一起发现文字的魅力,发现我们有喜欢某些文字和不喜欢某些文字的权利?
马克·吐温曾经说:一句真诚的赞美能让我多活两个月。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会思索怎么赞美,带着几分“刻意”的赞美,去赞美孩子的努力、发现,以及可能,这会不会有可能成为他的一个小小的信心来源,让他们不讨厌华文,觉得华文也没那么难,甚至愿意在华文搭建的世界里再走远一些?
华文学得好不好只是结果,可是在通往这个结果的过程里,教师和家长“有意”的表扬,以及学生因此产生的信心和勇敢,是更重要的。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