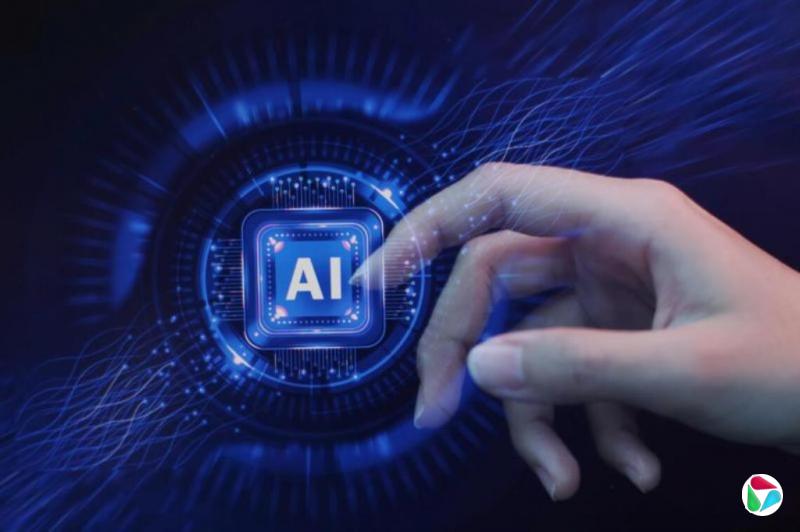
得知我要去新西兰休假,朋友说:“恭喜你,暂时不用牛马了,去看看真正的牛马如何生活!”
确切地说,在新西兰的不是牛马,而是牛羊。任由天下乱成一团,它们在漫山遍野悠哉吃草。突然乱入这个浪漫画面的,是某小镇社区的一则广告:“AI如何影响你的牛儿和羊儿?报名xx线上讲座!”
本以为新西兰这个“大农村”应该还是人工智能净土,却发现原来AI已经卷到这里。近期,新西兰媒体争相报道一项由养牛专业户自创的牛儿配种AI应用。这位爱好编程的现代农民,形容这个应用是“Tinder for Cows”,想必也真的是史上最“牛”的交友软件吧。
几天后,又在基督城的报纸封面读到这样一则报道:一名23岁的建筑设计师,入职一年多就遇上事务所大规模裁员。失业的他,决定从此放弃设计师梦想,转而修读护士文凭,相信后者会带来更稳定的职业。
建筑设计是很多人眼中的光鲜行业,几年时间啃下来的学历,含金量不低。也正因此,报道读下来令人唏嘘,可读着读着却也有点理解受访者所做的选择。
经济前景不确定甚至越发萧条,肯花钱找设计师的客户越来越少,公司一旦要精简人手,入行没多久的新人首当其冲。更不必说,很多设计如今几乎可以一键生成。
相比之下,护士仍是劳动力密集的领域。找人设计房子的人会少,但人总是会生病,随着人口老龄化,护理人员的需求只会与日俱增。
很多专业领域的初级白领,分分钟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不只存在于建筑设计领域。《纽约时报》今年5月一篇报道就指出,很多企业都开始采用一种“AI先行”的招聘策略——在聘用任何新人之前,先测试一项任务是否可用AI基本完成。《纽约时报》概括说,AI将带来一场初级员工的危机。
从去年AI发展开始小井喷,世界多国都出现大学毕业生转向蓝领赛道,或者根本不再笃信学历、直接投入“轻体力”工作的现象。在本地,一些拥有文凭的年轻人,也从事修理冷气、下水道等工作,靠双手赚取和白领工作相当的收入。AI可以进行水质检测,分析水道结构,但最终还是要用一双手去解决很多最日常的痛点。
我们常期待AI可以解放人手,解决人手短缺问题,可是AI和人共存的第一回合至此,我们更直接的感受是:人脑更容易被AI替代,反而人手不那么容易。事实上,不只是人脑,人心都能被AI模拟。情感陪伴与共鸣,是AI比人更擅长的技能。创意、巧思、同理心和深度……在这些本该是人类更引以为傲的方面,胜出的却未必是我们。
和几个不同领域的朋友聊起在工作中的AI应用,大家都有惺惺相惜的体验:有时AI工具几分钟生成的东西,比你我能想到的更精妙,而我等人类反而随即进入人工补足的模式,忙着将AI略显粗糙但有灵光的大手笔,修改成更贴近所在机构规范体例的模样,或是在尚不能连接共享的平台之间进行搬运。
一名在金融界有十几年经验的朋友,在经历最初几周可以利用付费企业版AI工具快速生成几十页报告的亢奋后,陷入一种倦怠和虚无,深感自我价值荡然无存。
很久以前,生成式AI刚刚开始进入大众舆论时,有个段子大意是说,曾经畅想AI帮忙跑腿、做家务,自己尽享闲情逸致、赋诗作画;结果是AI在赋诗作画,苦活累活自己干。
是不是我们真的成了牛马,而AI成了神仙?
当然,乐观来看,AI始终还是一种服务于人的工具,只要利用得当,它无疑是生活和工作的好帮手。陷阱在于,它是在让我们越来越懒惰,还是越来越勤奋?是成为快捷便利的答案提取库,还是激发更多好奇的始发站?到底如何才能突破这种既嫌弃AI的毛病,又自叹不如AI的窘境?
AI目前大概处于一种很好却又不够好的尴尬期,多数人只能向下补足,难以向上超越。要真正驾驭AI,答案不在追求AI技术,而是AI以外。当我们的大脑不可能比AI更快,知识不可能比AI更多,最有价值的就是双手和灵魂。
和AI共生的序幕已然拉开,如何避免看似驾驭AI、实则被AI奴役。如何成为那个神来之笔,而不是沦为牛马之力,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作者是《联合早报》影音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