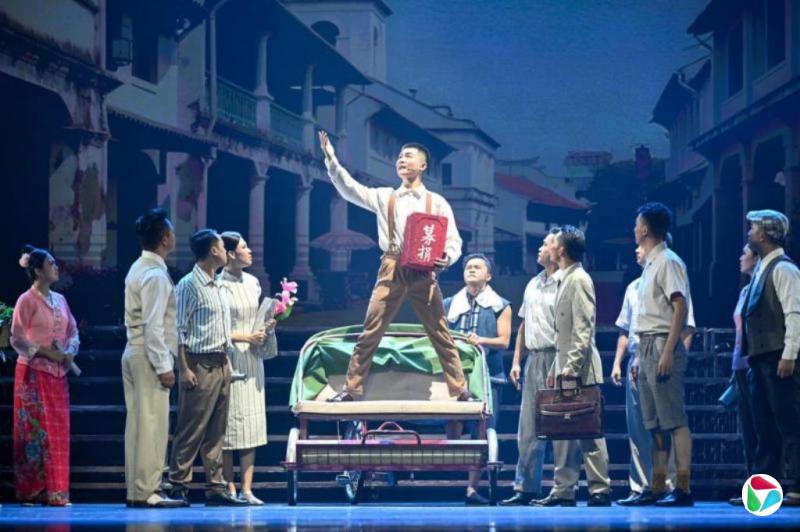
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故事最令人唏嘘。李月美又名李月眉,生于马来亚槟城,受陈嘉庚感召,要求报名参加南侨机工,但机工不收女性,她瞒着父母穿上弟弟李锦容的衣服,到一个无熟人的埠头报名。她的故事在抗战胜利后广为传播,新马媒体都以“当代花木兰”加以报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为表彰她的爱国精神,特题“巾帼英雄”四个大字的红绸锦旗赠作纪念。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战后与丈夫定居缅甸的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座谈会。当知道她就是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周恩来鼓励她把儿女带回祖国读书。她与丈夫多番争论后,在1965年11月把八个儿女带回国,留下丈夫杨维铨在缅甸。未料一家回国数月,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刚到广州就被下放到山区的英德华侨农场。她在审讯期间提到“小时候生活很好”,立即被批斗“那个时候(1949年前)生活很好肯定是资产阶级”,被令下田劳改。期间她写信向周恩来求救,周恩来也亲笔回信指示要加以解决。但此时周的亲笔信与何香凝的锦旗已无法救她,每天敲锣游斗。所到之处,人们拳打脚踢。到1968年8月28日深夜,她举起镰刀割脉又自刎身亡。八个儿女走投无路,在乡亲帮助下才回到海南老家。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郑民引述南侨机工的申诉书道:“他们在南洋原居地本是有家有业和有丰厚的经济收入的,当年是怀着满腔热血回国为抗日救国服务”,却落得政治逼害的下场,教人扼腕。
文革结束,大陆政府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侨机工的名誉才逐步恢复。
《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也写到:“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年文革后厉行务实政策。近年来遗留在国内的机工逐渐得到照顾,但是仍有部分尚被忽略者,亦在所难免。我们希望全体都能雨露均沾,安度晚年。”
若留意对南侨机工的纪念,不难发现,除了1947年建的吉隆坡广东义山亭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以及1951年11月11日槟城乔治市的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其他纪念碑大多建于1980年代之后,时间越近当下,纪念碑落成越多,如2013年3月4日新加坡晚晴园所建的南侨机工纪念雕塑、2013年8月13日柔佛古来所建南侨二战抗日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中国全境第一座纪念碑在抗战胜利前夕,就在昆明东郊郭家凹立有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殉职纪念碑,但在文革时被毁。最后在1989年7月7日在昆明西山风景区内重建,如今仍有不少活动。
这一回复常态的转变,既有从世界革命转向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政治需要,改善对待“华侨”的态度,也有助于招商引资,推动改革开放。
书面上的历史变成人们心中的记忆,要通过纪念、仪式、教科书等等的“记忆之场”(Site of Memory),我们记忆的历史模样,未必是历史原来的模样,但却与时代的声音息息相关。
1935年由聂耳作曲、田汉填词的《告别南洋》,在南侨机工群体里传唱极广;2007年有关海南籍机工的书籍,就用了其中一句歌词为书名:《再会吧!南洋》。
历史是有正义的,但总是会迟到。而迟来的正义,还是历史原本的模样吗?南侨机工在庆祝胜利的一刻,恐怕没想过等待他们的是更可怕的冷战风暴,尤其是留在中国的南侨机工,凄酸不足为外人道。“南侨”身份随着时代的浪潮起落,又拍进时代的暗流中,不知所处。
南侨机工的命运就像2016年纪录片《下南洋》主题曲《过番》里头,胡德夫用他独特沧桑的声音所唱的:“度春夏秋冬暑寒,盼明日好过今朝。忍苦累辛酸孤零,生死不过轮回煎熬。问家国乡邻故土,我生该当不平?!问天地君师人神,我命该破,该立该重头?悲喜,无常,涅槃,祈祷。”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