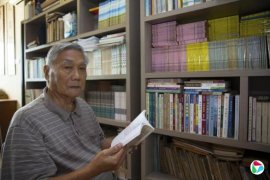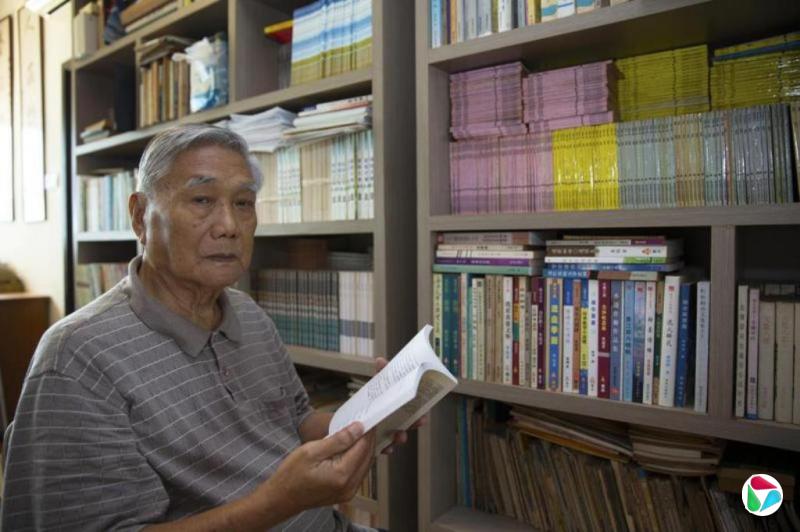
今年6月11日,《联合早报·言论》发表郭永秀文章《为学生出版华文作品集》,透露他经常把担任驻校作家时所接触到的优秀学生作品,收集在他参与编务的一些刊物中,如《锡山文艺》《新月》《赤道风》等。
郭永秀是锡山文艺中心主席兼《锡山文艺》《新月》总编辑,也是赤道风文化协会副会长兼《赤道风》副主编。以《赤道风》第114期为例,内收多所学校学生总共53篇作品,占同期刊物将近一半的篇幅,附有驻校作家郭永秀和陈帅评语的作品,分别为24篇和23篇。
此外,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的《源》杂志自2020年至今,也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开办的创意写作课的讲师林高所推荐和简评的学员(不限于中文系学生)作品,为新华文学做好赓续准备。
提起学生作品集中发表在文学刊物上,我联想到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新加坡文艺报》。2004年,应骆明之邀,我参与文协与国家艺术理事会联办的驻校作家计划,负责达善中学和海星天主教中学的驻校讲课,之后结集两校一些学生所呈交的篇章,润色后交给时任主编刘笔农于《新加坡文艺报》发表。
2002年,文协副会长刘笔农倡议每两个月出版一期小型报纸《新加坡文艺报》,每期寻求一位商家赞助千元的出版经费,不足余额由刘笔农垫付;出版后置于10家书店供免费取阅,一方面鼓励人们到书店看书,另一方面也鼓励创作。虽然刘笔农离世数年,但《新加坡文艺报》仍出版不辍,至今已成为学生作品的发表重镇。以最近两期为例,主编语凡刊登尤今在南侨中学、南洋女中、立化中学和中正中学(总校)的写作课学生作品,以及郭永秀和严文珍分别组稿的美廉中学和伟源中学学生作品。
从刘笔农倡办《新加坡文艺报》的往事中,我想起1970年中期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创办《文学月报》的用心。与其他文化人一样,黄孟文怀抱着社会使命感来领导作协。在写于1976年的《〈从〈文学月报〉创刊谈到当前文艺界的一些问题〉》文中,他指出当时社会缺乏阅读风气的普遍现象,大家一有空就想着消遣玩乐,例如他的一对夫妻朋友,两人都是大学毕业生,空闲时就会凑麻将脚进行方城战,没想到通过阅读充实自己。黄孟文当初是想编印一份大家都负担得起的健康文学刊物,来充实社会的精神粮食。
曾任文协会长30年的骆明今年4月18日离世,临终前希望子女能把故居改建成骆明文学馆,以永久收藏他生前所写的书籍、所编的书刊、他人评论他的文献、他的手稿、与国内外文友往来的书信,以及他数十年来珍藏的万册书籍等,并作为学术研究之用。
骆明交代后人创建骆明文学馆,明显有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无私心志。这与他在求学时期受惠于公共建设不无关系。求知欲旺盛的骆明在中正中学念初中和高中,从中一开始就爱上馆藏丰富的中正中学图书馆,一直到高中毕业。他在新旧千禧年之交发起创设新华文学馆,并在2022年发起创设中正人藏书馆,都与他在中学时代的美好熏陶紧密相关。
潮社名人黄诗通(1906年至1972年)生前热心社团事务,他认为社团是服务社会的平台,可以造福百姓;社团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应与国家紧密结合,作为国家的有力后盾。1969年,黄诗通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40周年纪念特刊》献词中指出,社团活动应扩展范围,摈弃保守思想,时时关心国家前途,配合环境需要,作为国家有力后盾,奖掖青年,拔擢新秀,灌输爱国思想,与新加坡兄弟民族团结一致,共同促进多元社会的繁荣,臻国家于富强之境。
另一怀有文化心的潮社儒商是杨绍和(1915年至1990年),他在担任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期间,曾从中国延聘潮剧老师来训练潮剧艺员,推广潮州文化;与此同时,会馆也积极响应推广华语运动。1980年,在会馆51周年庆祝宴会上,无论演讲还是表演都以华语呈献;会馆也筹办学生讲华语演讲比赛。
作为新加坡老牌俱乐部,醉花林也双线延续华族文化传统:一是在2012年由儒商李崇海创立的醉花林华语讲演会,以推广华语,发扬中华文化,提升会员的演讲与沟通能力,传承新加坡华族文化为己任;一是在2017年于时任司理陈可成的建议下,创立的醉花林潮曲潮剧艺术研究会,让潮州戏曲工作者在一起切磋曲艺,希望潮州戏曲文化能更广泛地推广开来。
今年6月28日,新加坡南安会馆举行《世界华人民间文化学刊》第三期发布会,会务顾问陈奕福重申,南安会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出版这本学刊责无旁贷;他甚至还建议,鉴于学刊论文作者群用心撰稿,会馆应该支付稿费。虽然支付稿费目前还处于刍议阶段,但这位儒商已在言谈间显露尊重辛勤耕耘的文化工作者的正面心态。
许多怀抱社会心的文化人以及怀抱文化心的儒商,前赴后继开展文化工程,让华族文化的发展与赓续更显得羚羊挂角,了无痕迹。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