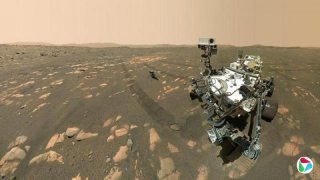小学时,学校食堂会不定期卖炒泡面,小碟三角,大碟五角。很多时候我会在上课前绕路到食堂瞄一眼,若发现这款炒面,下课的期待值瞬间拉满,上课动力也飙升。
当天一下课,我必定快步带小跑,闪过挡路人,第一时间到食堂买大碟的炒泡面吃。
这是我美好的食堂回忆之一。现在回想起来,那一碟炒面的香气和纯粹的快乐,依旧很鲜明。
当教育部日前宣布13所中小学明年起实行中央厨房供餐时,我不禁在心中呐喊:怎么可以?
诚然,学校食堂这些年来面对的挑战不易:成本上扬、人手短缺,在照顾学生营养摄取的同时,还得合理标价。中央厨房供餐似乎成了不得已的选择中,最现成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额外好处,比如食物卫生管理更集中、食物浪费情况更可控、学生也可省下排队买餐的时间。
可是啊,这些很务实的好处,都无法替代原本学校食堂文化的无形优点。
对我而言,学校食堂是我练习理财和学习延迟享乐的最初教室。零用钱要怎么用、省多少,才能吃好又有“余裕”储蓄,每天下课都在复习。偶尔,有同学没带钱包,我和朋友要么凑钱,要么一起把食物分享着吃。
另外,食堂也是生活技能的初级训练场,放水壶抢占位子、尝试没吃过的美食、与同学“以食物易食物”而尝到更多美食等的小日常,经历过的人自然懂得它们的美好。
这些同理心、价值观、生活技能,是每天在学校食堂一点一滴、无意识积累得来的。
学校食堂就犹如小型甘榜,人与人之间交流多,互动也直接。那浓厚且属于集体的人情味,虽然不是中小学生涯中的主旨,但肯定是形塑孩子内在素养的关键,也符合近日政府提倡“我们为先”的理念培养。
时代改变,学校食堂须转型也无可厚非。不过,在实现转型的当儿,应尽可能保留食堂原有的文化与氛围,例如现做现卖、现场选择食物、坐下一起吃。
教育部或校方也可考虑创新的食堂模式,像是餐馆一厨房多选择的经营方式,甚至是“无菜单料理”盲盒式点餐,让在数码世代成长的孩子,体验有趣又有温度的学校食堂。再说,吃中央厨房餐点的机会,往后多的是,何必提前到中小学时期呢?
教育部说,个人摊贩仍是学校食堂的默认模式。我小有安慰。在期许中央厨房供餐仅为过渡方案,不会再扩大的同时,我也希望有关官方能再研究各类津贴补助和转型的可能性,让这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学校一隅,能持续它原本的精神与美丽。别因大人的问题,让小朋友去配合与承担。
中学时,学校食堂卖印度煎饼的马来阿姨,会把一大勺的咖喱酱汁直接淋在煎饼上。一开始我对浸泡在咖喱里的煎饼,既怀疑又好奇,买了却迟迟不敢开动,直到同桌的学长说:“这样吃更香呢。”
果然,那样的吃法很香。那段回忆也一样。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