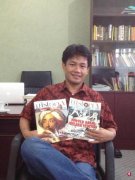著名文人蔡澜堪称一“逝”激起千层浪,马来西亚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对蔡澜的悼念文章也陆续见于各地报刊杂志。我们不禁要问,蔡澜有哪方面的特质吸引我们?他的离世到底反映什么?
读到中国作者魏水华的《我们怀念的不是蔡澜,而是那个贪吃好色理直气壮的年代》,或许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个现象。
魏文说:“他们在时代的背景板上挥洒着浓墨重彩的自画像,不怕颜色太浓,不怕格调太俗,不怕被人误会成老不修——因为他们从不伪装”“那时候,风流是可以说出口的,贪吃是种生活美德,而爱玩是种气质,不是罪”——这样的论述,说句实在话,有时还真会让人感到不适。在今天这样一个讲求文明、注重健康、强调涵养的年代,对任何一种表露真性情的言行举止,都不可避免要进行所谓“合理”的限制,否则就“天下大乱”了。应该承认,某些限制的确有合理之处,是必要的,比如我们总不能让人在一个严肃庄重的场合,肆无忌惮地爆粗口,以此来凸显他们的放荡不羁。但是,如果限制得过分,把所有人囚禁在既定处世公式的牢笼里,又不得不说会让整个世界缺乏生气。
蔡澜说过,他一生的理想状态是“床头有书,床尾有酒,床上有女人”。他还说:“这世上最没意思的事,就是假正经地过完一生。”由此可见,蔡澜不会被时人口中的伦理道德所束缚,他更多时候是随心所欲、“敢敢不正经”地过日子。同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词家黄霑,公然在电视节目里讲“咸古”(黄色故事),出版《不文集》,据说还有不少风流韵事,也算是身体力行地践行“敢敢不正经”的理念。
我无意提倡这样一种看似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只是想说任何一位正经生活的人,如果能够融入适当的趣味,跳脱某些人设的框框,未必是坏事。拿我们读文学的人来说,也知道文学作品不能一味板着脸说教,要有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主张的“不朽的笑声”。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大作《文心雕龙》里,也有专收游戏文的“谐隐篇”栏目。正经八百的东西固然要推广,对没有完全丧失底线的“油滑”,也不见得非得赶尽杀绝,它们是可以并存于世的。
易中天于2006年在中国央视节目《百家讲坛》品读三国故事,认为曹操胆敢说出“宁我负人,休人负我”的“狠话”,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在他看来,有不少人和曹操秉持的做人宗旨其实大体一致,却偏要给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宁人负我,休我负人”的假大话,伪君子比真小人更令人讨厌。学者秦晖也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最可怕的不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而是“满口仁义道德,成天男盗女娼”。说的和做的彻底相反,以天使之名行魔鬼之实,对社会国家必定造成难以想象的危害。
会出现这些情况,基本和人不懂得正确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不懂得正确平衡道德和欲望之间的砝码有关。明白这些,也许我们得说,蔡澜真正让人羡慕的是他在人生的多个阶段,都能在不违背大的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活出真我的风采,潇洒自如,从容不迫。因此他的离世能造成轰动,甚至让人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是马来西亚语文教师)